以前的我,覺得了解自己很重要。
從小是個學霸的我,在上國中時,考上了資優班。小學時隨便考都是全校第一名的我,在資優班時,拚了命的念書也只能排名全班中間。當”聰明、會念書”這個身分認同受到質疑時,我開始與憂鬱症搏鬥。
了解自己,才能訂出適合自己的道路和目標,我的一生中不停地靠著這個方法,擺脫憂鬱。當我不再是”聰明、會念書”後,靠著找到自己對美術的興趣,成功地塑造新的目標。有了方向,那種困在不見五指隧道中的窒息感,才慢慢消失。然而在我的人生旅程中,這種模式一再發生。所以我總是不停地向內探索,希望了解藏在蚊子後的大象、躲在角落的心靈孩子。
設定自我
人需要了解自己,是因為人們需要確定感。我們不喜歡未知、不可知,那種沒有控制的感受太不舒服。沒有方向、無所適從,這是很迷惘的感受,青少年往往深受其害。
了解自己似乎是很重要的事,甚至連神殿都寫上這句話。每個人也都很努力地在了解自己。幸運的人認為瞭解自己,於是能夠訂立目標,並努力去達成。不幸的人認為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或喜歡什麼,其實他們心底也是認為自己了解自己的,只是不知道這樣的自己能做什麼。
我很幸運地,在每次徬徨時,都能夠重新設下目標,重新定位自己。現在看來,這其實是再自然不過的了。自我,本來就不是真的,而是形塑的。你塑造什麼樣的自我,就會呈現什麼樣的你。 認為自己不知道自我能做什麼的,認為自己不知道自我的,就會持續在徬徨中渡日。認為自己找到自我的,就能奮力以這個形象過日子,並做相對應的事。
這麼說來,我們每個人都是演員。只是演出的角色,有自己設定的、有父母期望的、有社會期待的、或是在未知的不適中隨便將就的、也有人相信是神指定的。演出什麼角色、誰設定的,都不是重點。重點是自己是否能從演出這個角色中,感受到平靜和喜悅。
能不演任何角色嗎?我仔細思考這個問題,發現我的答案是不能。因為我畢竟有肉身,整個世界會用某種方式對待我,並期待我表現某種方式。我可以符合期待,也可以反抗。但反抗後也還是某個反叛的角色。即使遠離社會,遠離人群,也還在扮演某個求生的角色。阿迪亞香提在【受苦的力量】一書中也說,即使是耶穌、佛陀,意識上超脫於這個世界,但依舊扮演著人的角色。
追尋真我
來總結一下,我們需要一個目標,這讓我們覺得確定、有控制感。我們需要演一個角色,而且無論如何是無法擺脫的。這個角色可以自己設定、也可以讓別人或社會加諸於你,唯一重點是要讓自己演得快樂。
這時候有些人就焦慮了起來,因為在演某個角色底下,必定有個”真我”。那個”真我”在演出某個角色,必須釋放那個”真我”否則不可能有快樂。必須讓那個”真我”展現真實的樣貌,否則就是壓抑,或導致不幸福、甚至虛度人生。
我自己就是在青少年時,忽然有種沒有人了解我、在大家面前的我不是我的感受。那是一種心整個空掉的寂寞。我會感到寂寞,是因為我從未展現真正的自我,我展現的是我決定成為的自我,那個自我讓我呈現我以為最適合的樣貌。
展現最適合的自我,其實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我。 我到底是內向還是外向?為什麼我喜歡和朋友一起展現好人氣,卻又一個人窩在圖書館時最舒服?我到底是不是好學生?為什麼我喜歡成績優異、拔得頭籌的感覺,卻又想融入群體做一個酷酷的、不在乎學業的人?
那時候的我一頭栽進”自我成長”之類的書籍,每每讀到”創造自己的未來”等概念,就產生一股動力和滿懷希望,相信我終究能夠有幸福的一天。直到二十出頭,我忽然拐了個彎來到了靈修的領域。於是開始了”真我”的追尋。
我有種奇怪的執著,相信一旦我找到真正的自己,就能達到永恆的極樂。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相信某些宗教學說,單純地說我就是個靈魂,肉體的死亡會帶靈魂到天堂、地域或重新轉世。後來,我開始明白找到真我並不會到達永遠的幸福快樂,因為這是二元世界,有喜就會有悲,永遠的快樂是不存在的,我總是會將最小的快樂,重新定義為不快樂,然後拼命去把它提升到快樂的境界,永不停歇。儘管如此,我還是渴望找到真實的自我。
不需要了解自我
大家有過那種拚了全力去做一件事,卻發現那件事早已不重要的經驗嗎?某天,我忽然問自己,了解自我又怎樣?我的頭腦忽然短路,安靜了好久。既然,我明白無論如何都沒有永恆的快樂,那我到底為什麼要了解自己?
【人生四千的禮拜】一書中,提到當我們思考此生的意義時,我們希望並認定此生一定要非常有意義、一定要完成一些有影響力的大事。這是因為我們人類只有一生,而世界、宇宙則有成千上萬的人生。我們自己的一生,就是我們的百分之百。而我的一生,只是宇宙的億萬分之一都不到。於是作者說:
你拿人生來做什麼,其實根本沒那麼重要。你用你有限的時間做什麼,宇宙真的一點都不在乎。
乍看之下,似乎感覺到有點太消極。但仔細想想,我幹嘛要宇宙在乎我呢?我為什麼要把自己塞進”有貢獻、成功、偉大”這種箱子裡呢?我能不能過好我的人生、為自己負責就好?這麼說當然不是自私自利、目中無人。我的一生,只有我體會,就算對別人沒有幫助和貢獻,但只要沒有危害別人、只要我自己過得問心無愧,不也很好嗎?
【森林裡的資本主義者】一書中,作者說:
我意識到自己並不是那麼重要的人,沒有重要到需要如此努力地了解自己是怎樣的人。
我當然會影響我身邊的人,我當然某種程度地在這世上留下一點點痕跡。但當我停止以自己為中心,從全世界的宏觀視野來看時,無論我做什麼,都不會在這世上留下既深且久的影響。於是我舒了一口氣。我不需要去努力了解自己、努力挖掘和開發我的潛力、努力去發揮我的能力和影響力、努力去成為一個有用、有貢獻的人。我只需要做好我自己。
有些時候,我覺得我了解自己,就從這裡出發,做出我認為適合的決定,儘管也有不盡如意的時候。也有時候,我發現自己並不了解自己,但也明白,就算此刻了解,下一秒這個自我可能就改變了。所以完全不必為此感到焦慮。如果有必要,就再創造一個當下適合的自我吧。如果不適合,就大膽地捨棄。不必了解、定型、堅守,這樣的自我也算是了解自我吧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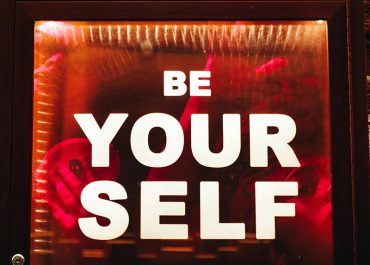
發佈留言